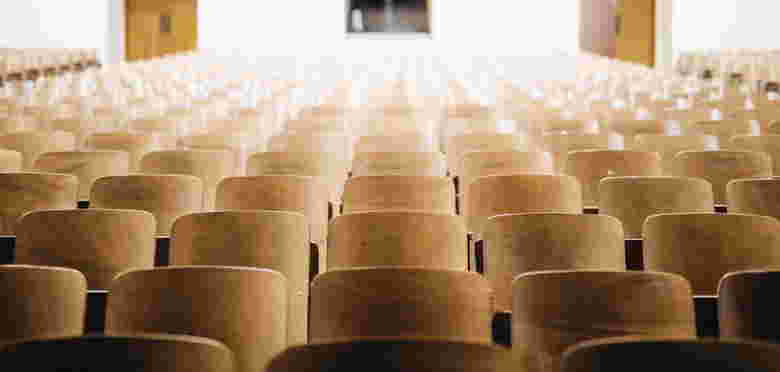政府提出对外国投资框架的变化,这些框架将使外国房地产投资者在另一名外国投资者未能达成定居点时购买外国房地产投资者。
在宣布变革时,财务主管斯科特莫里森部署了一个关于外国投资的熟悉的叙述,增加了外国投资,增加了房屋供应,并使“房屋更适合更多澳大利亚人”。
这个想法是与房地产开发游说者保持着侧重于政府释放更多土地来解决城市的复杂长期住房负担能力问题。
然而,研究人员之前已经揭穿了这个想法(见这里和这里)。他们的结论是,政府无法在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中提供。
政府侧重于物业行业的关注,呈现出更广泛的有关各方以及更加细致的贡献因素和解决方案套件。
目前的外国投资规则是一套钝的监管工具,俘虏了住房供应和全球竞争力辩论。
并非所有外国房地产投资者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外国房地产投资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些投资者经常在外国投资政策和公众辩论中混淆。
在广泛的条件下,有四个投资者团体。基于课堂的区分定义了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扩大中产阶级的人。他们被称为新的中产阶级。
不包括原代居所的一次性资产区别,将三个剩余群体分开。高净价值辛辛利有一次性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超高净值签约的资产控股超过3000万美元。超级超高净值签约在财富管理基金中至少有5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资产。
在没有关于哪些群体投资的细粒度数据和对城市和住房的差异影响的情况下,财务主任选择保护发展产业而不是城市内的人民和地方。
对各种投资者群体敏感的监管环境在澳大利亚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投资者以佩戴方式影响其主持人。
规范外国投资者,销售或资本
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外汇交叉如何依赖于谁是投资资本,资本正在投资的财产以及资本正在转让的投资车辆。
外国资本的到来并不总是伴随着城市新的永久居民的到来。因此,投资者以佩戴方式与局部基础设施和形状的外壳供应互动。
与超高净值投资相比,新中产阶级和高净值投资者对城市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
超级,超高净值纯粹可以是“自由浮动”投资者,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旅行,在各种全球城市购买房地产。罗兰阿特金森认为这一本集团对主人街区的忠诚毫无忠于。
超高净值投资者可能会在多个居所之间移动,并向邻居的附属物在他们的房产上。新的中产阶级和高净值投资者可能住在,或送他们的配偶和/或孩子们住在他们所拥有的房子购买。他们往往忠于城市或社区所处的城市。
外国投资者的个人动机也很重要。他们可以远远超出财务考虑因素。
西班牙奢侈品房地产参展商在北京豪华房地产展示(LPS)展示期间的潜在投资者。超高净值签约可以全球商品以进行投资物业。照片:Hwee Young / EPA如何
外国投资者受到澳大利亚存在的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与他们自己的移民计划,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和澳大利亚房地产所担保的财务保障有关。
因此,投资和居住地位将塑造邻里,城市,也许甚至是国家。
伦敦高度超高净值投资者的社区似乎(或可能)缺乏人。随着当地的赞助人数下降,这些郊区的当地企业已经无法维持。
新的中产阶级和高净值投资者可能会通过居住地改变社会结构,教育机构或邻里或城市的就业景观,以获得好坏。
国际证据表明,一些投资者将占据他们的财产,其他投资者将其放在租赁市场上,一些购买多百万美元的奖杯住宅,而其他投资者则购买额外的奖杯房屋,而其他投资者则会在缺席所有者和褪色业务附近增加住房供应。
因此,外国投资者对住房供应的影响与每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有关,他们携带澳大利亚的资本金额以及它们如何投资它。
需要更具动态的外国投资规则
住房供应和全球竞争力争论已捕获外国房地产投资辩论。两者都太简单,需要使用额外的声音,政策和数据来增强。
政府通过“经济利益”在繁荣时期和“经济必需品”在困难时代的论点来证明他们的外国投资和商业移民政策。
这些自上而下的叙述将外国房地产投资源于当地经济,具有次要效益,如通过有针对性的技能迁移和业务发展提高住房供应和工作增长。
政府需要了解外国投资如何将城市从头塑造。这包括:外商投资如何影响这些物业所在的当地社区的人;开发人员如何改变他们建造的住宅,以适应外国投资者;改变教育机构如何塑造外国学生投资;以及一家正在寻找同一房地产市场的家庭的第一家购房者的经验。
本文基于在国际住房政策杂志上全球房地产学习特别问题的研究。
达拉斯罗杰斯,城市研究员研究员: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与城市研究计划研究所
本文最初发表在对话上。阅读原始文章。